现实主义看竞争 中美防意识形态冷战(组图)
发布 : 2021-4-04 来源 : 明报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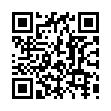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发布 : 2021-4-04 来源 : 明报新闻网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左图为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9日在北京向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强调当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

美国总统拜登3月25日在白宫开记者会,形容中美竞争是「21世纪民主与专制之较量」。(法新社/资料图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上月23日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右)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碰手{打招呼。后者在当日会晤中表示,中俄等专制国家正在挑战国际秩序。(路透社)
拜登:中美「21世纪民主与专制较量」
「这是21世纪的民主政权与专制政权之较量。」拜登上月25日任内首场记者会谈到中国和俄罗斯时抛出这论述,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相信「专制统治是未来潮流,民主体制无法发挥作用」。
拜登及其团队原已强调要跟在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上月印太和欧洲外交攻势已体现这点。另一边厢,中国加强拉拢俄罗斯、伊朗和匈牙利等被西方视为专制或有此倾向的合作对象,《纽约时报》为此发表题为「专制政权的同盟?中国想领导新的世界秩序」文章探讨。
上述变化令美国外交决策圈更关注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潜在角力。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库珀(Zack Cooper)和布兰兹(Hal Brands)上月的受注目《外交政策》文章指,华府或只有到中国政权失败才算胜出中美竞争,警告中共或认为由民主大国或价值观主导的国际体系属其存亡威胁,故寻求更全面修正。同月另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二人更表明「中美对立是价值观较量」,华府须更重视结合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见另稿)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泊汇向本报称,中美会否走向意识形态对立的地步,完全视乎由谁去解读双方的战略竞争,目前拜登政府由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决策者去运作,欧洲大国亦然。他表示现实主义者认为竞争是受中美力量变化所驱动,故不会视中国和西方关系由意识形态对立来定义。他承认布兰兹等部分美国现实主义学者呼吁采取意识形态竞争来提高美国战略地位,但在主张意识形态对立「并非目标、只是手段」,用以在国内外动员应对力量竞争。
高敬文:两极秩序已成结构性现实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早前向法新社称,世界正迈向两极秩序和新冷战,又表示民主政体如今在新疆、香港以及中国人权问题上建立「神圣联盟」。他接受本报访问时维持悲观预测,称欧盟主流意见认为世界是迈向多极而非两极秩序,但欧盟高度意识到需跟美国更密切合作来抗衡中国,保留对华筹码。他直言,倘若中方持续向台湾、南海声索国和日本作军事施压,欧盟难以跟其合作,进而难以推动多极世界——贸易和人权议题情况一样。他又指中方持续攻击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体」,变相动员反华的欧盟公众舆论。
他不讳言恐怕美国(与西方)跟中国的新冷战和两极秩序已变成结构性现实,「没有欧盟或其他地方的国家可以真正躲避……但到头来,新冷战总比新热战好吧?」
有关中美战略竞争会否走上意识形态角力的忧虑,可追溯至特朗普政府强调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等论述,外长王毅去年7月更斥美方「蓄意挑起意识形态对立」。数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说再质疑,中共从未忽略中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差异,表明华府今后同样不能忽略这点。
这说法引起中国外交圈子警惕,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去年10月撰文,探讨防范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直言中方只能靠自身单方作为来防范新冷战风险。他强调不搞意识形态之争是中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战略原则,拥有维护有利国际环境、减少国际合作政治障碍、增强国际战略信誉和防范陷入新冷战等战略意义。
张泊汇:务实约束战略竞争成关键
张泊汇则提醒,另一重要因素是中美双方「能否以务实方式约束和管控其战略竞争」,如果做不到,竞争中不自觉地浮现的意识形态因素将成为「自我实现预言」,然后成为战略对立的真正驱动力。他相信中国和西方领袖都意识到这危险,又强调中国战略家大多通过现实主义视角看待中美战略竞争,「现实主义者永远相信竞争和合作可以共存」。
